6、浴火方能重生,“江西之困”与“大悔大悟”
本期节目的文案6800字,音频约24分钟。
前情回顾
被长沙官员逼走衡阳的曾国藩,一心练兵,待他日再找机会一雪前耻。一介书生,投笔从戎带兵,举步维艰,不管是筹饷,募兵,训练还是制度建设,到处都是困难。曾国藩曾用蚊子背大山,蜈蚣过大江来形容自己的艰难处境。
湘军倾注了曾国藩的全部心力,他要以此拯救国家于危难。但是咸丰皇帝对此不以为然,在练成之前多次要他出兵抗击太平军,都被曾国藩断然拒绝,这也让咸丰对自己的厌恶是与日俱增。
在这期间,他的挚友和恩师,都因为自己的按兵不动而先后兵败自杀,他的内心承受这怎样的巨大压力,我们可以想见。但也正是因为他的长远谋划,才让湘军免遭轻进覆灭之灾,为日后平定太平天国积蓄了力量。
第二年,湘军出师,兵分两路,一路由塔齐布带领进攻湘潭,另一路由曾国藩亲率,攻打靖港。因为情报出现重大失误,步入了太平军的陷阱,让胜券在握的曾国藩,迎来了首战惨败,想到自己的心血顷刻间化为乌有,他羞愤难当投水自尽,还好被身边的护卫即时救起。
让曾国藩没想到的是,另一只部队在湘潭大捷,这是太平军起事以来清军最大的一次胜利,也是天平天国命运的一个重大转折点。
捷报传来,咸丰大喜,嘉奖曾国藩,授他在湖南调遣百官之权,从根本上改变了他在湖南的政治地位。
那曾国藩为什么能练就“神兵”,湘军与正规军相比,有这么几个制度上的创新。
- 1、厚饷制,打消全军的金钱顾虑,让将士们都把心思全部用在打仗上。
- 2、“将必亲选,兵必自募”,用制度解决之前需要用道德来约束的问题,极大的增强了全军的凝聚力。
- 3、选将选读书人,用兵用纯朴汉。相比于孔武之力,曾国藩更看重精神的力量。
- 4、注重思想政治教育,因为一支军队如果拥有坚定信仰,必然就可以激发出惊人的能量。
这样的建军思路是非常高明的,湘军日后的所有功绩都是建立在这些制度创新之上。
曾国藩忍辱负重,最终一雪前耻,长沙之辱再一次强化了他百折不挠的性格特点,他自己也说,天下事,有所激,有所逼,而成者居多,智慧经历越多的苦难才会越发的明晰。
湘军的意外崛起,让大清看到了起死回生的希望,按理说曾国藩应该成为天下的中流砥柱,尽可呼风唤雨,可是呢?不用说权倾天下了,曾国藩马上连自己的兵权都保不住了。
一句改变命运的话
话说,湖南首胜之后,湘军气势大振,经过一番修整,1854年44岁的曾国藩,率水路大军从长沙出发,进攻湖北。一路势如破竹,很快就收复了两湖最大的城市武汉,迅速扭转了全国的败局。
捷报送到皇帝案前,咸丰高兴得不知如何是好,于是任命收复湖北的曾国藩为湖北巡抚。
这个任命对于在外带兵的曾国藩来说实在是非常非常的重要。之前他举步维艰的一个最大的原因就在于自己在地方上没有实权。大清朝各省的实权其实是掌握在省委书记和省长,也就是说总督和巡抚手里的,他们才是全省官僚系统的绝对主人。可以说下级官员的身家性命都掌握在他们手中,自然对督抚是唯命是从。
曾国藩虽然与巡抚一样是二品大员,但是地方官对他确熟视无睹。因为他没有提拔官员的权力,就无法左右他人的命运。而无论是筹饷,招兵,选将等等的这些军事,曾国藩需要地方官僚系统的支持,没有实权他自然就调度不灵。
咸丰皇帝自然很清楚曾国藩需要的是什么,那在发出了曾国藩的任命状之后,他召见军机大臣通报了这一喜讯。咸丰兴高采烈的说:没想到曾国藩一介书生,能建此奇功,是我看错他了,他不光能吹牛,还是有真本事的。
这时一位军机大臣,耳语说:曾国藩本来不过是一个在家守孝的退休官员,如同一介平民,可他振臂一呼竟然能集结起这么多人为他卖命,所向无敌,这恐怕并非国家之福吧?
到这句话,彻底改变了曾国藩的命运。
大清朝有两条根本的政治原则:
一是“满汉之分”,清代皇帝在民族身份上的认同是非常清楚而敏感的,重满轻汉自是必然。所以无论是封疆大吏还是军队领导,满人一定是占有绝对的主导地位。
二是“强干弱枝”,就是中央的权力一定要完全凌驾于地方势力之上,这也是我们之前所说的兵一定要为国有。
这两条政治原则,在承平时代巩固满人统治和中央集权当然是没有问题的。但是现今呢?满族人的勇武已经在温柔乡中消磨殆尽了,现在可天下存亡之秋,重用汉臣,放权督抚将帅是挽救大清命运的唯一途径。
然而,这些迂腐无识的建议,偏偏就是能入咸丰的耳朵。咸丰听军机大臣这么一说,素然一惊,汗毛倒立。
是啊,我们大清素来兵为国有,而湘军却兵为将有。现在你曾国藩保我没问题,但他日倘若你起了异心,你的湘军谁人可挡?你现在已经有了兵权,万万不可以再给你地方行政权。
咸丰已经顾不得出尔反尔了,赶紧又发了一道上谕:你专心打理军务就好了,地方的破事儿我再找别人去办。
曾国藩在收到任命书的时候非常的高兴,今后湖北全省都听他调遣,他可以以此为根据地,从容规划消灭太平天国的大业了。他上疏恭谢天恩之后,按照惯例还是要稍微推辞一下的。
咸丰收到折子,顿时后悔自己收回巡抚职务的上谕发的太早了,你曾国藩肯定会辞谢的啊,我应该等到这个时候再顺水推舟,同意你的请求。现在是自己出尔反尔,朝令夕改,难免脸有点疼。
咸丰自作聪明的在这道折子上批示说:我早知道你会辞谢的,所以呢,还没等你辞的时候,我就洞察先机不让你当了。然后话锋一转,我上道上谕已经任你巡抚职务,这道奏折你竟然没用巡抚头衔,你这是违抗圣旨之罪,我要让军机处对你严行申饬。
你看,咸丰是不是鸡贼得不可思议。
这道朱批批回来,曾国藩瞬间懵逼。万万没想到,自己的辞谢都还没到北京,职位就被收回了。他可真是倒吸一口凉气,可见朝廷对他的防范已经到了什么地步。
与咸丰的战略分歧
咸丰不仅不给曾国藩权力,还不断的打乱曾国藩的用兵计划。
我们说,一个高明的战略家,一定需要有长远的战略眼光,可惜咸丰却并没有这样的眼光。
太平天国定都南京之后,咸丰的皇位岌岌可危,他的注意力被限制在这里了。他认为战争的关键就是攻克南京,之后整个天平天国就会自然瓦解。所以他的战略是“先伐根本,再剪枝叶”。他围绕这个战略,抽调一万多精兵建立了江南江北两座大营,想用最快的速度在南北夹击之下拿下南京城。与此同时他不断的要求曾国藩尽快与江南江北大营汇合,一同攻打南京。
但是南京地势险要,面对太平军的严防死守,想要短时间内攻破坚城,根本就不可能。
而曾国藩认为,情况远比咸丰以为的要困难得多。天平天国掌握着长江中下游几座重要城市,依靠长江这条运输线,把各省资源整合在一起,让自己成为一个有生命力的整体,因此他才难以平定。对于这整个体系来说,南京并不是最关键的一点。
曾国藩的战略正好与咸丰的相反是“先剪枝叶,再伐根本”。东南大局的关键在于武汉,现在湘军已经拿下武汉,占据长江中游险要之地,有了立足的根本。以两湖为根据地,积累足够的力量之后,再顺江而下,取九江,夺安庆,最后才是图南京。
事实证明这是一个非常高明的战略,而且最终就是按照这个战略清王朝才取得了最后的胜利,也正是因为如此,曾国藩才那么重视湖北巡抚这个职位。
湖口大败
人生海海,潮涨潮落,曾国藩很快又要迎来自己人生中的下一个至暗时刻了。
1854年的9月,咸丰就要求曾国藩向重镇九江推进。
在两湖地区的一系列辉煌胜利,让曾国藩也有些过于自信,九江位于潘阳湖与长江之交,战略位置非常关键。
曾国藩举兵进入江西之后,所向披靡,长驱直入,直取九江。这一次,在九江太平军可是做了非常充分的准备,要与湘军在此决一死战。
太平军的将领也冥思苦想怎么才能打败湘军,他们发现湘军之所以这么厉害,很大程度上是依仗水上的优势,欲战胜湘军,必先破其水师。湘军的水师分为大船和小船两部分,一个灵活一个笨重,二者相互配合,取长补短。针对这个特性,太平军制定了一个策略。
两边水军对峙的地方叫做湖口,是长江与潘阳湖的一唯一交汇口,一边是宽阔的长江,另一边则是广袤的潘阳湖。两水之间是一个极其狭窄的交汇口,只有小船才能通过。
湖口之内的太平军用小船对江面上的湘军水师进行不分昼夜的骚扰,虽然没有取得什么实质性的战果,但就是要你日夜都不得安宁。不断的被骚扰,又求战不得,湘军水师的焦躁之气是越来越大。
有一天,对太平军实在是忍无可忍,湘军出动了120余艘小船带着2000多人杀入潘阳湖内,追击太平军战船。结果被太平军抓住机会,封堵湖口,修建工事,安装大炮,将这部分湘军全部困杀于湖内。
那外江上的大船呢?没有了小船的配合,如同鸟失去了翅膀一样,丧失了作战能力,限于被动挨打的局面。
太平军趁着夜色,从容的发动了大规模进攻,湘军水师大败亏输,曾国藩坐在舢板上督战,不准退却,但毫无作用,靖港的情形再一次重演。
曾国藩自己的坐船都被太平军攻破,他身旁的贴身官员全部被杀,连他自己都差一点成了俘虏,他在太平军逼近的时候又一次跳水自杀,还好被自己人给救起来,逃了出去。
从此之后,武汉以下的江面上,再也没有了湘军的船只,太平军重新控制了长江航道之后,发动战略性反攻。等到来年的2月,太平军重新夺回了武昌,湖北大片地区再次沦陷。曾国藩一年多的战果得而复失。
湖口兵败之后,湘军水师几乎全军覆没,只好把全部希望寄托在陆军上。面对太平军在九江的死守,尽管湘军昼夜苦攻,死伤无数,但战事毫无进展。曾国藩手下的大将塔齐布竟然被战事逼得焦灼剧增,吐血身亡,年仅35岁,曾国藩抱着塔齐布的尸体大哭了一场。
拿下武昌后,太平天国第一悍将翼王石达开带兵杀入江西,对湘军展开了强大攻势。面对石达开的进攻,湘军接连败退,最后曾国藩被死死围困在南昌城内,情况非常的危急。
就在南昌指日可下,眼看曾国藩呼救无从,即将殉国之际。石达开接到命令撤回南京,去攻打江南大营。被围困南昌的曾国藩这才得以绝处逢生。
江西之困
在江西的这段时间,不仅仅是在军事上陷入危机,在政治上也是“长沙之辱”的再现。
湘军出省作战,军费只能就地筹集。这个责任需要由江西省的地方官僚系统来承担。当时的江西巡抚叫做陈启迈。在他看来,你湘军跑到我的地盘上吃我的粮饷,那当然要对我唯命是从。虽然他根本就不懂用兵,但依然对曾国藩指手画脚,呼来喝去。曾国藩哪能受得了这个,根本就不听他的。
这就惹火了陈启迈,不听我的,那就别想吃我的饭,于是断了曾国藩的粮饷。
于是曾国藩拍案而起,上奏弹劾,陈启迈被革职查办。接下来的事情又重复了曾国藩在湖南的经历,这次参劾反而让江西官员变本加厉的针对他。
接替江西巡抚的叫做文俊,是一个旗人。你曾国藩来江西搞事情,那陈启迈怎么对你,我依然怎么对你,江西全省官员在文俊的率领下团结起来到处给曾国藩设障碍、使绊子。不仅官僚系统不支持你,不管你找谁,是找乡绅捐钱,还是招募人才,谁敢支持你我就收拾谁。
在这样的打压之下,湘军长期陷于饥困。为了吃一口饭,有人甚至还丢了性命。有一个叫做毕金科的将领,地方官员告诉他,只要你拿下了景德镇,我给你发粮饷。毕金科一向莽撞,现在又是穷困到了极点,只好决定一试。他率领的一千人进攻景德镇,在敌人的重兵严防之下,全军覆没。曾国藩知道之后气愤不已,但又无可奈何。
从1854年到1857年,在江西这段时间,曾国藩在军事和政治上都选入绝境,这也是他一生当中最最痛苦的一段时间。他在给朋友的书信中用了4个字来形容此时的感受,叫做积泪涨江。就是说我受到的委屈,我积攒的泪水,让江水都上涨了。
丢失兵权
就在曾国藩痛苦万分之际,突然接到了父亲曾麟书去世的消息。这个噩耗此刻倒成了他摆脱困境的托词。他立刻上疏回家守孝三年,当时说的守孝3年也不是今天的36个月,而是27个月。还不等皇帝批复,他就已经把军队抛在江西自己回了湖南老家。
皇帝当然不会准他守孝三年,在回复中催促他赶紧回去带兵。曾国藩干脆借此机会向咸丰摊牌,一股脑的把自己这几年来压抑已久的心中苦水全部倒了出来,如果不给我督抚大权,这个兵就真是没法带了。
他认为自己已经把委屈和困难说的够充分了,皇帝没有理由不给他这个卖命的走狗一点支持。
可没想到,咸丰皇帝长期以来的不满,让他在这个时候和曾国藩较上劲了。他干脆就顺水推舟的同意曾国藩在家守孝三年,实际上就是解除了他的兵权。
咸丰只所以敢这么干,是因为当时发生了天京事变。天平天国最高领导人是天王洪秀全,但是军政大权其实是掌握在东王杨秀清手里。消灭了江南大营不久之后,杨秀清野心膨胀,图谋最高权力,引发内讧。洪秀全诛灭了杨秀清,石达开也领兵出走,天平天国内部人心涣散,军事形势瞬间逆转。
所以现在看上去天平天国已经是秋后的蚂蚱,蹦跶不了多久了。既然如此,你曾国藩还有什么资本和我较劲呢?正好趁这个机会让你滚蛋。
这当头一棒把曾国藩打的是晕头转向。他万万没有想到,自己苦战数年竟然是这样一个结果。他的那些宿敌听到这个消息,又有话说了:你之前以唯我独忠之态,睥睨众人。现在你曾国藩如此要挟皇帝要官,不管什么原因,都有违臣道。于是大骂曾国藩是假忠义,他自己也有口难辩。
最让他痛苦的是,建立不世功勋的机会,就这样从自己眼前溜走了。此时正是天平天国由盛转衰之际,而他偏偏这个时候被解除了兵权。而自己的曾经的那些部下呢?都因为军功飞黄腾达了。像是胡林翼都已经当上了湖北巡抚。可自己还是个二品在籍侍郎,没有任何升迁。
曾国藩估计天平天国在一年之内就会被荡平,到时候论功行赏,唯独没有他这个湘军创始人的份。
大悔大悟
自己失去了这么一个永载史册的机会,怎么能不懊悔莫及呢?这次挫折对曾国藩的打击真的非常大。赋闲在家的他夜不能寐,性情大变,整天的生闷气,动不动就骂人。先是数着江西的一帮文武官员骂,然后又挑几个弟弟的毛病,像是曾国荃,曾国华、曾国葆,都没少挨骂。惹不起我躲得起,于是几个弟弟都找借口离家出走了。弟弟走了,曾国藩又揪着几个弟媳妇骂。言语粗俗,蛮不讲理,学者圣人的风度荡然无存。
发泄了一段时间之后,曾国藩把自己一天一天的关在屋子里,开始反思这么多年来为官带兵生涯中的种种情形,渐渐的,他的内心平静了下来。
他反思到,自己遭遇“长沙之辱”、“江西之困”,在官场上屡屡碰壁,撞的鼻青脸肿,不光是因为皇帝昏庸,同僚不作为,其实自己的个性、脾气和处事方法上也存在着诸多的问题。
回想自己此前的为人处世,总是怀着强烈的道德优越感,自以为居心正大,人浊我清,因此高己卑人,锋芒毕露。
他翻阅当年的旧书信,发现当时武昌告急的时候,自己写给湖南巡抚骆秉章求援的一封信。在当时,他觉得自己的这封信写得字字有理有据,可是今天再读来,却发现字字如锥如芒。你去求援,不仅没有任何商量的口气,反而略带讥讽之意。怪不得当年骆秉章批评他刚愎自用,听不进别人的意见,所以也自然没有人愿意给他出主意。当时曾国藩觉得不以为然,现在回想起来,真是说到了他的痛处。
他还反思到:自己不仅仅是面对同僚的时候,以圣贤自名,以小人视人,就连对自己的亲兄弟都成天一副“唯我独尊”的神气,处处批评教育,弄得当年曾国荃、曾国华来北京投奔他,没几天就回家了。
设身处地,推己及人,被曾国藩冷眼以对的同僚,自然也就用冷面甚至是辱骂来对待他。
于是,曾国藩在家里给朋友们写信,请大家给自己多提意见,帮自己总结经验教训。在1857年底的时候,曾国藩的一位幕友,叫做罗汝怀,给他寄来了一封长信,信中罗汝怀是这么说的。
如今官场世风日下,确实没错。但是你打算摒弃体制内的力量不用,赤手空拳把事情做成,这可能吗?你一个人逆众人而独行,难以成事啊。
你统领湘军的时候,最大的困难在于筹饷,要做成这件事情,一要靠百姓,二也要靠官员。靠百姓,让百姓不埋怨你,这你是知道的。但是要靠官员,也不能让官员怨恨你,这你就不够注意了。你筹饷,抽税都踢开官僚系统自己亲力亲为,这是根本就行不通的。
你看,罗汝怀这个人虽然名气不大,但是这封信写的直率而有见识。
曾国藩终于认识到,行事过于方刚者,表面上看似乎是强者,实际上却是弱者。真正的强者是表面看起来柔弱退让的人。正所谓“天下之至柔,驰骋天下之至坚”“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,以其善下之”,“大柔非柔,至刚则无刚”。
中国社会中那些曾国藩之前看不起的虚伪、麻木、圆滑和狡诈,是在这片土地上生存的必须手段。只有必要的和光同尘,圆滑柔软,才能顺利的通过每个困难,只有海纳百川,兼收并蓄,才能调动各方的力量,助我到达胜利的彼岸。
蛰居在家的这两年,被曾国藩称为自己的“大悔大悟”之年,他在经历了“江西之困”被解除兵权,这个人生最大的挫折之后,也迎来自己一生中最大的一次蜕变。
上天最终还是没有亏待曾国藩,很快他就再次出山,这下他性格大变,他在日后的官场上,如何成就自己内清外浊、内方外圆、内圣外王之道的呢?
下期节目,我继续和您说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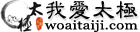 我爱太极
我爱太极